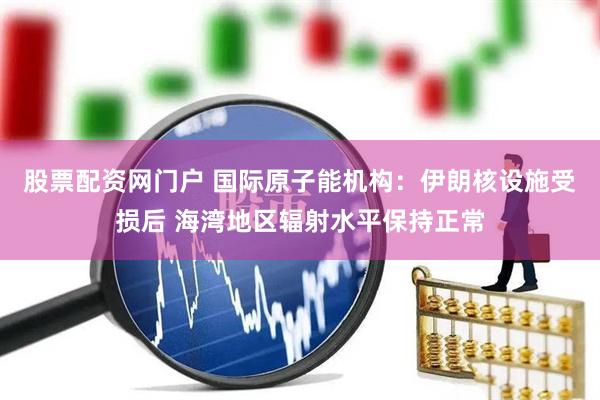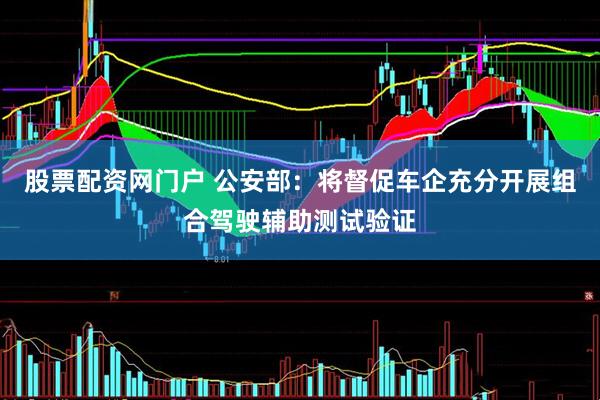邸双杰股票配资网门户,一位以家乡唐县的中山国历史文化为诗歌创作主题的诗人,近年来根植乡土文化,创作了近300首诗歌作品。
邸双杰的诗歌创作以中山国历史为精神原乡,通过重构民族迁徙轨迹与文明记忆,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。
其诗作如《中山吟》以白狄鲜虞人的迁徙史诗为轴心,将“跋山涉水寻找梦里的家”的集体记忆转化为民族精神的图腾;《委粟山怀古》则通过地理坐标的消逝(如委粟山、倒流河)与遗迹的在场(青铜马、玉人形俑),形成“记忆的考古学”——当“中山的遗迹荡然无存”时,传说与文物成为承载历史的双重载体。这种创作既非单纯的历史复述,亦非抒情式的怀旧,而是以诗歌为镐,挖掘被时间掩埋的文化层理。在《寻找一匹失踪的青铜马》中,文物失踪隐喻记忆危机,而《中山篆》则通过书法符号实现文化正名,彰显诗人对断裂文明的重连渴望。其诗歌本质是一场“精神还乡”,将个人书写升华为民族记忆的修复工程。
展开剩余71%邸双杰的诗歌意象系统呈现出多维度的象征网络,自然、人文与季节意象交织成厚重的隐喻体系。
自然意象中,委粟山、倒流河、马耳山不仅是地理坐标,更被赋予文明断层的象征意义——倒流河以逆向流动隐喻历史轨迹的错位,而委粟山则成为凝视历史的两只眼睛,在《一年到头》中“装满我的期待和泪水”。人文意象则通过中山长城、法果寺遗址、青铜马等符号构建记忆场域,如《记梦》中“城墙上的酸枣树挽留我”,以植物意象将历史遗迹人格化,形成文明与个体的情感羁绊。季节意象则强化时间张力,十月秋光与十二月冬雪形成沧桑对仗,《中山殇》中“城春草木仍深”以反常的春日荒凉突显历史悲怆。其意象组合更具独创性:在《梦回中山》中,“神游故国”的梦境将“打夯筑城”的古代劳作与“搬运文字”的现代书写并置,形成时空折叠的镜像结构;而《中山玉人形俑》则通过文物拟人化,让玉俑成为“讲述不屈往事”的叙事者。这种意象系统既延续了古典诗歌的比兴传统,又以“委粟山的两只眼睛”等超现实表达拓展了现代诗的陌生化效果,最终构建出兼具考古学精确性与抒情诗张力的独特美学。
邸双杰诗歌的情感张力根植于对文明创伤的直面与超越,其悲怆底色中始终跃动着文化自觉的火焰。
《中山殇》以“城春草木仍深”的荒凉意象,揭示历史记忆的集体钝痛,而《中山魂》则通过“浩气传千”的呐喊完成精神救赎。这种矛盾在《记梦》中尤为显著:“梦中打夯筑城”的血肉辛劳与“醒来搬运文字”的使命重负形成双重煎熬,最终在“坟前泪流满面”的仪式中释放压抑千年的文明阵痛。其情感表达具有鲜明的对抗性:一方面以《寻找一匹失踪的青铜马》的失踪隐喻记忆危机,另一方面又以《中山篆》的书法符号重构文化自信。这种张力在《一年到头》的循环时间叙事中达到高潮——十二个月的等待与缺席,最终被“旌旗插上城头”的象征性胜利消解,形成“以缺席证实在场”的悖论美学。诗人将个人乡愁升华为民族记忆的守护,如《故事》中“与鲜虞人共白头”的拟古想象,既是对消逝文明的挽歌,亦是对当代文化根脉断裂的补偿性书写。其情感考古始终贯穿双重维度:在“法果寺碑刻认得我”的个体对话中完成自我确证,在“千日醉灌我半夜兴奋”的集体唤醒中实现文明传承,最终形成“以泪为墨,以痛为铭”的独特抒情范式。
唐县是“战国第八雄”中山国肇始建都之地,是赓续2500多年的中山文化的起源地和发祥地。白狄鲜虞人在太行山东麓中人城(今唐县西北委粟山一带,即中山城)建都,成立了中山国,后来迁都灵寿(今平山三汲乡一带)创造了比肩战国七雄的灿烂文明。唐县中山国文化是千年古县唐县的文化瑰宝,是唐县人民具有文物、文字史籍可考的历史根脉,亟待发掘、弘扬,因之作痴梦中山组诗。
作者:邸双杰,网名:青山磊落,男,70后,籍贯保定市唐县南城子村,现居保定市。199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,系唐尧诗词楹联协会会员、保定市作协诗词艺委会副主任、保定市作协会员、保定市竞秀区作协理事、保定市长城保护协会会员、保定老调艺术传承促进会会员、保定市地方文化发展促进会理事、保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、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、唐县中山国文化研究会会长。
发布于:河北省粤友钱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网门户 1948年,2名地下党被抓,60岁老太用三寸金莲一脚踹开牢门:快跑
- 下一篇:没有了